今天是:
中文版救助机构动物领养成难题
[ 字号:大 中 小 ]
2012-03-09

部分想领养的人都是想找些名贵品种,当看到救援队收养的本地土狗后,一般都不愿意领养。
2009年3月,中山市出现了第一个动物保护民间组织––由几个自愿者自发组成的“小动物救助协会”。
一年之后,因资金及人力匮乏而得不到有效支撑,该组织黯然解散,在中山市动物保护组织历史中昙花一现。
2011年10月,“中山动物保护救援队”再次由几个自愿者发起成立,是目前中山城区唯一一个动物保护民间组织。眼下,他们也遭遇了与“小动物救助协会”同样的困局:救助站的动物“只有收养没有领养”,而救助站则“有名无分”,其成长空间再一次面临了极大的考验。作为第二个中山本土的民间动物保护组织,它是否会重蹈覆辙,像前一个团队一样黯然解体?同样的困局,中山动物保护救援队希望能够找到不同的破解之道,并成功突围。
困局从“只有收养没有领养”开始
大鳌溪村阴巷街的一个静谧的小巷子里,有一个旧式的民宅。在很多的时候,这个角落跟其他村屋没有太大的差别,直到中午11:30前后,里面才传出一两声狗叫声,那是正在吃午餐的动物们争抢食物发出的声音。
这里就是中山动物保护救援队目前固定下来的救助站。为了避免扰民,救助站的运作尽可能保持低调。目前,这个救助站已经搬了3次地方,换了3代管理员,并正如去年年底成立之初那样,无时无刻不面临资金、资源、管理等方面的运作短板。
“最大的问题是,只有收养,没有领养。”中山动物保护救援队发起人迅姐说,自从救援队正式成立以来,他们共接收过52个流浪动物,但仅有2例成功的流浪狗领养记录、7例流浪猫领养记录。而事实上,从博客、论坛等途径得知中山动物保护救援队并前往咨询领养事宜的人并不算少。为何成功领养的数字变得如此“悲壮”?
“首先有一大批人是希望来这里领养名贵犬种的,看到本地土狗和‘老弱病残’的,一般都掉头;还有一个是不能接受支付300元的进口疫苗费用和绝育费。”虽然300元的疫苗费和绝育费让不少网友诟病,但迅姐坚持这么做。在她看来,一方面这是文明养宠物的一种实践,另一方面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借领养之名来套取猫狗的商贩。
于是,流浪动物只进不出,很快将一个最基本的空间容纳问题推向瓶颈––“并不是我们不想救,真的是放不下了。”
为了呼吁社会热心人士的领养,迅姐和队友们曾多次在他们的微博及其他媒体平台呼吁,但效果甚微。被送进来的流浪动物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小,怎么办?无法从领养方面突破,救援队考虑转向狗舍扩容项目。
志愿者垫付经费已成常态
目前救援站内共有十几只流浪狗,其中有4只还在诊所接受治疗。这些被救助回来的流浪动物,大部分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在救援队给笔者出示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少则300元、多到6000元的治疗费用。比如今年春节期间抢救回来的“爬爬”,因后肢和腰被折断,整个治疗期近3个月,前后花费了6000元。
还有日常开销需要应付。从救助站的账目上可以看到,目前该站每月的开销最低3300元:租金500元,看管员工资1800元,水电约200元,粮食800元–900元。
救助站主要经费来自于义卖、会员捐赠以及淘宝网上一些热心人士的资助。但大部分时候,救援队的几个管理员都需要自己掏腰包垫付。在救助站2011年12月的账单明细上,可以看到几个管理员的垫付款项,8名管理员一共垫付了4000元。
经费吃紧一直是中山动物保护组织的瓶颈。早在2009年,中山市也曾出现过由自愿者自发组织的“小动物救助协会”,但因人力资源及资金严重匮乏,该组织只支撑了一年便黯然解体。目前,救助站为了扩大收容规模,正计划启动第二期的狗舍项目,但同样被困在资金问题上。
放眼广州土华等其他城市的动物保护组织,接受捐赠仍然是其中一个主要的资金来源。但作为一个新生的民间组织,如何获取有效、合法的受赠渠道,并建立良好的公信力呢?和3年前的“小动物救助协会”一样,中山动物保护救援队将希望放在了成立正规的社会团体、取得规范命名上。
“有名无分”难建公信力平台
中山动物保护救援队目前有8个管理员,所有管理员都是通过兼职形式参加救援队工作:白天工作,晚上到救助站开会、讨论、记账或者清理。在大鳌溪村阴巷街这个简陋的村屋里,见证了他们一次次试图解决困局的突围。
事实上,通过官方管理部门来给救助站的公益性质以一个权威、合法的命名,是中山动物救援队一直以来的心愿。但按照《中山市社会团体筹备及登记程序》规定,最大的障碍,是没有业务主管单位。
嘉华透露,他们曾向多个部门咨询过,但都找不到相关的主管单位。“林业局只负责管理野生动物,畜牧兽医局只负责管理家禽,农业局也表示流浪动物不在管理范围。我们也希望能有个官方的名分,有规范化的管理和运作,并通过这些监督和管理来培育我们这个组织的公益性质。”嘉华如是说。
去年11月份,《关于广东省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出台,明确从今年7月1日起,对社会组织规范管理推出新规定,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不再需要挂靠主管单位。“能不能成立,我们都尽自己的能力坚持,能救多少是多少。有时候也会天真地想,我们这么努力会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这样救助站就不用撑得那么辛苦。”嘉华说,他们等待今年的7月,是否能给中山城区这个唯一的动物保护组织的困局一个答案。
-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宠物食品用品检验检疫分会率团赴欧洲...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宠物食品用品检验检疫分会率团赴欧洲...
-
 宠物分会副会长及常务理事单位荣获“中国质量诚信企业”称号
宠物分会副会长及常务理事单位荣获“中国质量诚信企业”称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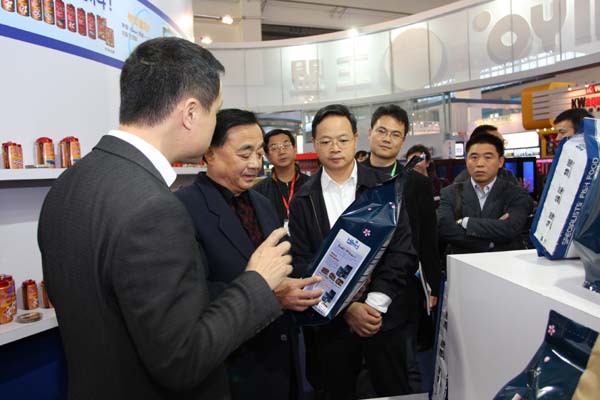 葛志荣会长参观宠物分会副会长单位共鳞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break;
葛志荣会长参观宠物分会副会长单位共鳞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break;
-
 葛志荣会长参观宠物分会副会长单位浙江天下实业有限公司展台
break;
葛志荣会长参观宠物分会副会长单位浙江天下实业有限公司展台
break;
-
 葛志荣会长参观宠物分会副会长单位厦门吉信德宠物用品有限公...
break;
葛志荣会长参观宠物分会副会长单位厦门吉信德宠物用品有限公...
break;
-
 葛志荣会长参观宠物分会副会长单位烟台中宠食品有限公司展台
break;
葛志荣会长参观宠物分会副会长单位烟台中宠食品有限公司展台
break;
-
 葛志荣会长参观宠物分会副会长单位温州佩蒂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break;
葛志荣会长参观宠物分会副会长单位温州佩蒂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break;
-
 葛志荣会长参观宠物分会副会长单位青岛美今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break;
葛志荣会长参观宠物分会副会长单位青岛美今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break;
-
 葛志荣会长参观宠物分会副会长单位佛山达洋宠物用品制造公司...
break;
葛志荣会长参观宠物分会副会长单位佛山达洋宠物用品制造公司...
break;
-
 热烈庆祝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宠物食品用品检验检疫分会成...
break;
热烈庆祝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宠物食品用品检验检疫分会成...
break;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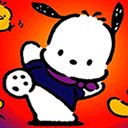 宠物分会网站展示通知
宠物分会网站展示通知